
先說一則今年年初的事——
每年春節后都會發生的制造業“招人荒”,今年比以往更令人矚目。
畢竟這次缺人的主角,是富士康。
富士康都如此,其他制造業工廠想來更難。
按照往年的經驗,這段荒蕪期本不會持續太久,時間長了,工人們就會像遷徙的候鳥一樣,陸陸續續從老家飛回工廠。
而如今,流水線上的工人反倒成了流水線,導致制造業出現貧血甚至大面積失血。
那么工人究竟去哪兒了呢?
一條不起眼的線索,給了我們靈感。
去年,美團點評研究院發布《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》,與前陣子新聞里刷屏的“大學生送外賣”不同,數據顯示,三分之一的騎手在送外賣之前,職業身份是產業工人。
并且,一部分目前還在工廠里的工人,已經選擇在業余時間兼職送起了外賣。
所以,制造業招不到人,是因為工人都去送外賣了?
不妨做個對比。
1. 就業人數
從就業人數來看,東莞市很有發言權。
老話說得好,“東莞堵車,全球缺貨”,東莞可謂是 “世界工廠里的世界工廠”。
然而,根據艾媒咨詢統計,自2013年到2018年六年間,東莞市蜂鳥騎手數量增長了31倍,與之對應的是,東莞市人社局在年前公布的2019年東莞市企業節后用工需求信息顯示,800多家企業節后將空缺崗位近10萬個。
一個門庭若市,另一個則是門可羅雀。春節后,能夠回到制造業企業上班的工人,數量大約是去年的90%,而外賣小哥卻逐年增多。
2015年,美團外賣騎手人數僅為1.5萬人,但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,日均活躍騎手人數已接近60萬人,而餓了么旗下蜂鳥騎手的注冊人數則早已突破300萬人。
2. 勞動力來源地
從來源地來看,確實存在外賣行業分流制造業勞動力的現象。
75%的美團外賣騎手和77%的餓了么騎手來自農村,大多來自河南、安徽、四川等三個省份。這三省均為勞動力輸出大省,只是過去都往工廠里扎堆,如今也持續為外賣行業輸送人員。
3. 年輕人吸引力
這一點,制造業異常羨慕外賣行業。
外賣騎手的平均年齡在26-30歲左右,35歲以下占比近70%。
而根據富士康工業互聯招股說明書的記錄,27萬名員工中,30歲以下的員工占到59.65%,看上去還算和外賣行業旗鼓相當,但這個人數相比2012年,已經整整縮減了三分之一。
制造業越來越不吸引年輕人,對其打擊最為致命。一個失去年輕人的行業,如同一潭死水,發展進步均無從談起。
然而,外賣行業其實只是大量分流勢力中的冰山一角。
截至2018年,全國快遞員總數超300萬人,加上近些年互聯網公司在生鮮配送、餐飲供應鏈等等不斷發力,未來所需勞動力只會更多。
考慮到兼職,就又有一股勢力冒頭:已登記在案的、合規的網約車司機,截至目前共計373萬人。
或許,這早已經不是什么分流,而是直接抽血了。
2016年,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曾批評房地產行業,認為2008年以后,地產建設與銷售吸收了大量勞動力,變相抬高人力成本,對制造業造成了巨大的沖擊。
如今,外賣、網約車、快遞行業等也在做同樣的事情。
餓了么的全職騎手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,算上兼職騎手,月平均也有4000-8000元左右,能力出眾的“單王”月收入甚至可達3萬元。這組數字已遠遠超過2017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均薪資3813.4元。
而據新聞報道,2018年富士康工人的月平均工資為6000元,結合性價比,也早已跑輸外賣行業。更何況,普通的制造業工廠根本拿不出富士康這么高的工資。
結果就是:人往高處走,制造業則招不起人。
與此同時,人還會隨著產業發生流動。這就得參考參考美國了。
1850-1970年,美國傳統制造業所在的“鐵銹八州”,人口從1023萬快速增至7203萬,而1970年后,它們的人口增量嚴重放緩,反倒是加利福尼亞州、德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的人口發生了激增。
1970年到2017年,“加德佛”三州人口從3794萬增加到8883萬,是同一時間段“鐵銹八州”人口增量的9倍以上。
到底發生了什么?
“鐵銹八州”州如其名,是美國傳統制造業集聚地,而“加德佛”三州則以先進制造和現代服務業為主。1970年后,隨著西歐、日本和中國的崛起,美國傳統制造業逐漸走向衰落。此次地理大遷移,其實質是就業人口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結果,史稱“服務業革命”。
盡管中國在地理上尚未有美國如此明顯的人口遷徙,但產業遷移卻正在發生。
2012年,中國的第三產業首次超越第二產業,且比重逐年抬升。
因此,外賣行業從制造業搶人,從本質上說,屬于中國式服務業革命中的一個具體場景。
革命就意味著制造業缺人之勢將難以逆轉,只能轉移或轉型。
從2013年開始,中國就有大量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東南亞。
國內紡織業制造龍頭東南亞擴產情況
至于轉型,我們再說回東莞。
2014年,就在外賣小哥人數激增的同時,一場“機器換人”三年行動計劃在東莞悄然展開。機器換人后,一家企業同樣的產能,用工量從8000多人減至1800人。
截至目前,東莞這一舉措,共幫助企業節約用工近20萬人。
放眼全國亦如是。2013年,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,并連續五年保持第一。
那么,如今還有人,尤其是年輕人,愿意當工人的嗎?
流水線上的藍領工人,普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當工人;在某地的招聘會上,95后表示“工廠一線已經不太適合年輕人”。
在2018年820萬畢業生最想就業的行業里,我們看不到任何制造業工人的影子。
不過,在歐洲,有人卻愿意當一輩子的工人。
與傳統意義上的工人不同,他們是擁有與機器生產相配套能力的技術工人,也是如今轉型升級中的中國制造業最缺的人才,企業招聘薪資均在萬元起步。
是啊,外賣也好,快遞也罷,他們是比流水線上的工人更掙錢,但說到底,大家最終賺的都是辛苦錢、而技術工人的職業含金量顯然比外賣小哥更高。
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這場服務業革命倒逼著制造業升級,而制造業的升級,最終,又會在未來的某一時點,帶動服務業發生進一步變革。
或許,這才是這場“搶人大戰”背后的最優解。
【推薦閱讀】
一個東莞民營企業主的自白
臺積電和富士康:信息產業的心臟和軀殼
富士康和比亞迪的“代工廠之爭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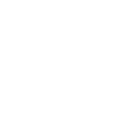 客服
客服
 熱線
熱線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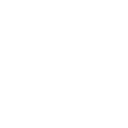 微信
微信